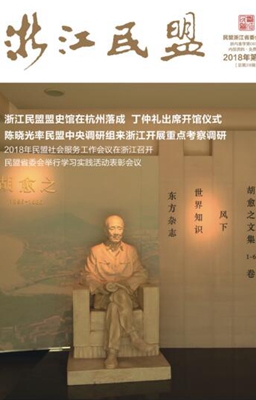四月下旬的一个周日,又是个大晴天,我开车回到老家,看见老父亲又在忙着挑水浇菜地了。我停好汽车,快步走到地头,跟父亲打招呼:“阿爸,你又在浇水啦!”
“嗯!你回来了。”父亲把手里的粪勺放回粪桶,抬起手臂揩了一下额头,无可奈何地说,“唉!这老天爷已经连着十来天不落雨了,种好不长远的丝瓜、黄瓜、茄子、番茄等苗苗,已经全部打蔫了,倘若再不浇水,全要枯掉啦!”
“那你一趟挑两个半桶水好了,不要累着了;现在年纪大了,不比年轻的时候,还是保重身体要紧啊!”我提醒父亲道。
老父亲是1936年底出生的,今年已经84岁了,身体还算硬朗。他做了一辈子农民,跟土地有着很深的感情,看不得让土地撂荒。一年四季,他总是忙个不停,种这个、收那个,一刻也闲不下来。
我祖父早年得了肺结核病,在那个年代是不治之症,40多岁就英年早逝了。我祖母只生了我母亲和姑妈两个,母亲要招一个上门女婿。而我父亲家里弟兄三个,他排行老三,就顺理成章到石家入赘做了女婿。于是,父亲刚一入赘就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,里里外外都要他操持。
父亲高小毕业,能写会算,在他那个年代,也算是半个秀才了。在我的记忆中,父亲打得一手好算盘;有时晚上拎着算盘出门,去帮着生产队查账。也有的晚上,本家的大伯拿着在部队当兵的儿子来信,让父亲帮着写回信。大伯简单地口述几句,父亲就写满了一页纸;父亲写完念了一遍,大伯点点头同意,这样回信就完成了。
其实,父亲早年曾经是一名煤矿工人。1958年10月,当时老家属于海宁市通元乡,父亲和本乡的几个年青人被长广煤矿公司招收为正式职工,在东风岕井从事井下采煤工作,那艰苦程度可想而知。大约过了两年半,父亲他们几个实在忍受不了高强度的劳动,于1961年4月自动离职回家务农了。
在生产队挣工分,父亲总是挑着重担。春耕大忙时节,父亲挑起猪羊灰下田;早稻插秧了,父亲挑起秧把穿梭于秧田和大田之间;到了收割季节,父亲把潮湿的稻谷挑到晒场;等到要交售公粮了,父亲挑起晒干扬净的稻谷送入粮仓。而在冬季兴修水利的时候,父亲主要是负责挑土方。
那窄窄的田埂上,那泥泞的小道上,那高低不平的砂石路上,留下了父亲勇挑重担的身影,肩膀上的扁担发出“吱嘎吱嘎”的声响,陪伴着父亲奔波劳作……
20年前的3月里,我祖母去世了;17年前的10月里,我母亲也离开了人世。祖母和母亲先后离世,两人只相差三年半时间。我父亲从最初失去亲人的阴影中慢慢地走了出来,一个人默默地守在老家,守着几块土地,春种秋收冬藏,一刻也不闲着。
望着父亲挑水浇地的身影,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40年前父亲送我去湖州上大学的情景。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海盐的交通远远没有现在这样四通八达。尤其是我的老家石泉,出门远行是很不方便的。1980年9月中旬的一天,父亲送我去上大学,从我的老家石泉到湖州市区,先乘澉浦到海宁县城硖石的小客轮(途中停靠通元、石泉等地),然后从海宁坐火车到嘉兴,再转乘长途汽车从嘉兴到湖州,这样辗转多次才到达位于湖州市人民路的嘉兴师范专科学校。
从我们家里到轮船码头,从轮船码头到火车站,从火车站到汽车站,从汽车站到学校,这一路上,父亲挑着我沉重的行李,迈开大步走在前,我在后面紧紧相随。平时父亲总是习惯用左肩挑担,左肩挑累了就用右肩轮换一下。我几次要与父亲轮换,父亲总是说“我来挑,我来挑”,他浓浓的父爱就蕴含在这一句话中。这一天,我们大清早从家里出发,一路换乘奔波赶到学校,早已是黄昏了,人民路上已华灯初放。父亲的辛苦自不待言,我的内心对父亲充满了感激之情。
1983年7月,我从嘉兴师专中文科毕业,由海盐县教育局分配至通元中学任教。从我的老家石泉步行到通元中学,大约有6公里的路程。8月下旬的一天,父亲又挑着我的行李送我去工作单位。……
父亲的扁担有长有短,长扁担是树木做的,短扁担是毛竹做的。父亲的扁担朴实而坚韧,象征了父亲勤劳而辛苦的一生。
正当父亲节来临之际,谨以这篇短文献给我的父亲,祝老父亲健康长寿!使得我们兄弟姐妹能够有更多尽孝的机会。